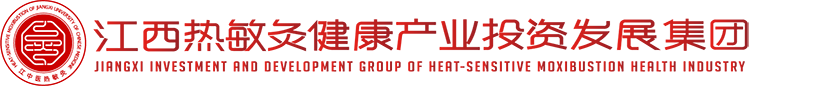
0791-83068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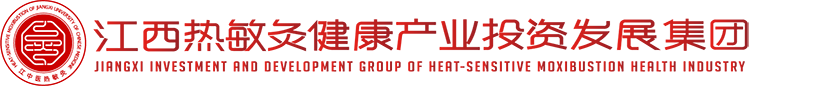
0791-83068301

蒋玉伯(1891—1965),字成瑞,湖北省枣阳县人。著名中医学家,曾任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副校长、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
1951年起,蒋玉伯先后担任武汉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南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专门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人大代表。
他著述颇丰,主要代表著作有《中国药物学集成》《针灸疗法经穴证治备考》《内科学讲义》《妇科学讲义》《药物学类纂》《内科纲要》及其门人整理的《蒋玉伯医案》等。
蒋玉伯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中医,同时接受新式学堂的熏陶。他1906年毕业于湖北省枣阳县高等小学堂,继赴武昌湖北文普通中学堂求学,又考入湖北法政专科学校。1921年毕业后被推荐至北京图书馆从事编辑工作,颇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3年他在北京考取中医开业执照,正式在北京行医。1927年正值军阀混战期间,他迁回武昌专业中医、悬壶济世。1933年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迁武昌北城角,蒋玉伯任该校教务长兼内科和药物学教授。1938年8月,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停办,他携全家返枣阳县,创办了私立复兴中学,任该校董事长。1939年12月,蒋玉伯经旧友介绍随军看病为军法官,后又委任为均县、竹山县县长。因深感当时军政官员相互倾轧,派系斗争激烈,蒋玉伯1941年7月辞官,逐迁家至郧阳,专业中医诊所行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武昌城行医、经营药铺至全国解放。
束发立志白首不渝
蒋玉伯生于清末,当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在其父的影响下,蒋玉伯立志学习中医药。他在《中国药物学集成·自序》中写道:“余自束发读书鉴于国医之衰微,即在志于斯道,每于课余之暇,辄读医书,不忍释手。”
在北京图书馆任编辑期间,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涉猎很多医学著作,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日后的临床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蒋玉伯任民国湖北省竹山县长时,正值当地瘟疫流行。他一边为官断案,一边为民治病,求治者络绎不绝。尔后,他根据疫情处了两方:一方用以预防,一方用以治疗,让人抄成“布告”,张贴于城门,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因此,他辞官离竹山县时,送行者长达一里多路。
蒋玉伯出门看病,进门看书,不畏严寒酷暑,潜心攻读医学著作,刻苦钻研医学理论,精心为人治病。他广罗博采,善取各家之长,触类旁通。如他历经十余寒暑,四易其稿,所著的《中国药物学集成》一书,35万余言,不仅引用了古今中外医学著作及医学文献资料达96种之多,而且记述了个人的临床心得体会,该书于1935年由上海国药研究社刊行全国发行。《申报》专版介绍该书为“国药科学化之巨著,国药界空前的杰作”,评价“就其数十载教授经验,研究心得与十余年心血,成此精要巨著”。上海市国医公会负责人盛心如为该书作序:“《中国药物学集成》一洗旧时流弊,参以最新学说”“可谓博而约,简而赅,浅而显,用而切,诚为将兵之韬略也……医者可备为肘后。”当时轰动海派医界,著名医家丁仲英、夏应堂、谢利恒、顾谓川、张赞臣、王仲奇、蒋文芳等九位医家作序题跋,赞誉为“医学导师”“国药指南”。
“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蒋玉伯为中医事业精勤不倦,就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整理、撰写医案,以留给后人。
投身教育桃李芬芳
蒋玉伯从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一个国家,一种事业之兴旺,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他为中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3年,他在担任湖北国医专科学校教务长期间,充分发挥办学之才干。他治校强调一个“严”字,狠抓一个“管”字,并极力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他经常勉励学生:“要珍惜学习机会,学好本领,为继承和光大中医事业,为四万万同胞服务。”
他十分重视临床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求教师授课时,尽量运用典型病例进行直观教学,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他在学校里开设了一个门诊室,由教师轮流带学生临床见习,并要求学生做到“眼到、口到、耳到”。门诊室每天接诊患者三五十例不等,既是临床教学的课堂,又是为社会服务的场所,深受学生和患者的欢迎。
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他在办学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据曾在该校就读的夏幼舟主任(已故)回忆:“当时该校的医学著作齐全,参考资料丰富,可说是应有尽有。”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自创办至1937年共招收学生7届193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为湖北省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蒋玉伯担任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副校长和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期间,已年逾花甲。他除担负大量的临床任务外,还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指导他们的业务学习。他一生培养了成百上千名学生,这些学生承继了蒋玉伯为中医事业献身的精神,发展了蒋玉伯的学术思想,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曾在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听过蒋玉伯课的已故国医大师、湖北中医药大学李今庸教授曾目睹蒋玉伯在光化县(现湖北省老河口市)为国民党上将李宗仁治病的经过,心生敬佩之情;已故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院长、全国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黄绳武教授,回忆当年就读于湖北国医专科学校的情形,他说:“我之所以能在中医妇科学方面有所造诣,应感谢先师蒋老的指点。”像李今庸、黄绳武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博取众长卓有见地
蒋玉伯善于取古今中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在《从中医阴阳学说探讨人生理病理和诊治规律》一文中指出:“阴阳学说含义甚广,义理幽深,变化无穷,既为人之根蒂,又可以指导临床实践,掌握治疗规律。”并告诫医者“必须穷究此中奥秘之理”。在临床实践中,他不存在门户之见,不持骑墙之说。对待前人经验,他既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有个人创见。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重视中西医双重诊断,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按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治疗。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常说:“治病之法,有虚实寒热、气血上下之分,透得其情,按脉审证,依法立方,则治一病之法,可以旁通治诸疾,故方贵简约则熟练而力专,繁多而散漫而力薄矣!”
蒋玉伯不仅擅长内科、妇科,而且擅长针灸,治疗中他常“针药相济”,速取奇效。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个人长期的临床实践,探索出一些带规律性的针灸疗法。如胃痛病者取足三里、梁丘;心脏病者取神门、通里;咳喘、胸痛者取太渊、鱼际、孔最;肝区痛者取行间,配阳陵泉;脾区胀痛者取阴陵泉;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者取巨虚、上廉;小肠痛者取巨虚、下廉;膀胱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者取委中;肾脏绞痛者取涌泉配肾俞等。上述疗法应用于临床,均取得较好的疗效。
蒋玉伯不仅精通医理,而且对药物学的研究颇深。他说:“医知病理,而不知深究药物,不能收十全之功,古人之用药如用兵,则药物之重要可知矣!”因此,他主张方与药,似合而实离,常于临诊自立处方。他认为,“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其药有一二味与药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故善医者临证,必先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法定方来。”“凡立一方,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不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
临床治疗中,蒋玉伯常以单方单药取效、药廉力专。如他用白蔹以治疗妇女阴中肿痛,赤白带下;用慈菇以治恶疮肿块,内服外敷均可;木鳖子煎水熏洗内外痔、脱肛、痔漏、红肿流脓,收效颇捷;玉簪花根捣汁敷治乳痛等,用之颇验。
医德高尚死而后已
蒋玉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历代医家的高尚医德思想,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医德医风的范例。蒋玉伯一生接诊的患者成千上万,既有孙中山等政界重要人物,也有国际友人,但更多的是一般老百姓。无论是谁,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普同一等”。
他在1925年2月25日的北平《顺天时报》上发表《对孙中山病状之研究》一文,其中写道:“余告中医应诊者,宜考察精确,审慎处方,标本兼治,勿养痈贻患,以误病者,而贬损中医之价值。”他对前人的经验,注重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做到既继承又有创新。如在药物研究方面,他认真查阅了从《神农本草经》到历代本草著述,从中医学著作到日本汉医经验方,以及《俚俗药方集》《国书集成》《汉法医典》乃至《满蒙杂志》等。他为民治病,终身勤奋,哪怕是在重病垂危之际,也不懈怠。
1965年初,蒋玉伯因长期积劳成疾,患重病在家休养。湖北省卫生厅为此写了一张“布告”,张贴于他家门首,以谢绝前来求治的患者。但患者仍不断求诊,他来者不拒,带病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蒋玉伯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中医事业,医德高尚,死而后已,因此备受人们的崇敬。他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案例,可以说每一例都闪耀着其医学思想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前,蒋玉伯曾治疗一妇人,年二十八,患吐血症,历三日不止。每天吐血半痰盂。邀请德国医生克立氏诊治,用药内服、注射毫无效验。患者人事不省,于是辞去不诊,后经蒋玉伯诊断,望其色如黄表纸,胸置冰囊,头戴冰帽,目不识人。诊其脉洪大,尚微有力,知系邪火扰动血分,吐虽多尚未至于脱,宜用凉血降火行瘀之剂,使瘀与热从下窍出,而血自不上逆。方用生地黄、麦冬、杭芍、广三七、大黄末。令除去冰囊冰帽,药煎成后,将三七、大黄分2次随药冲服,一服稍安,二服即止。次日复诊,病者即能抬头道谢。又于前方去大黄末加龟板、炒阿胶、炒黄柏,连服5剂而愈。
又治国际友人马某,女,48岁,患心绞痛,心痛时发热,汗出,卧床不起,诊其脉左寸口涩,右关弦数,此为心血不足,邪火内燔所致。《金匮翼》卷六中有云:“心主诸阳,又主心血,是因邪而阳气郁伏,过于热者痛”。诊为热厥心痛,治以养血凉血、清热止痛之法,并以针刺,以速其效。先泻通里,补神门、间使,应针而安,拟失笑散加生地黄、牡丹皮、菖蒲、远志、当归,少佐川连等药,服3剂其痛已止,可下床游玩,经短期治疗,有显著效果。
他从不因病人的社会地位、贫富不同而异,总是全神贯注,不掺杂念,至意深心,详细检查,对症用药。尤其对贫苦的患者,经常施药不收费。
早在1927年,他在北京西直门外行医。有一外国领事介绍一位叫亨利的外国巨富来治病。患者因咽喉右侧长一肉瘤,逐渐溃烂化脓穿孔,靠橡皮管插入胃中进流质食品,痛苦非常,曾求治于欧美各国名医,皆无效。亨利曾说:“谁治好此病,愿赠家产一半,作为谢资。”蒋玉伯替其诊断后,用自制的“六合拔毒生肌散”内服外贴,数诊后伤口逐渐愈合,饮食如常人。一天领事送来酬金表示感谢。蒋玉伯十分诧异,问患者为何不来复诊。领事说:“患者已于今晨回国。”蒋玉伯十分叹息地说:“为医者在治病耳,岂贪财乎!”
蒋玉伯治学严谨,对技术精益求精。他学识渊博,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热爱的中医事业,备受人们的崇敬。正如他的好友题挽所写:“妙手回春救世人有生难忘,著作流传使后代受益犹生。”他不仅是一代名医,而且多才多艺。医学、哲学、法律、文学无所不通,琴棋书画无所不为。有位著名科学家曾说:“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这段话,用于蒋玉伯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本文资料为笔者已故父亲周金林先生收集整理,特注明以表怀念,周伟 湖北中医药大学)
稿件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稿件链接:http://www.cntcm.com.cn/news.html?aid=232142
责任编辑:刘君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